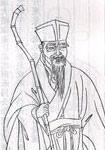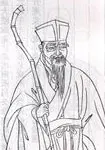杨慎(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杨廷和之子,汉族,四川新都(今成都市新都区)人,祖籍庐陵。正德六年状元,官翰林院修撰,豫修武宗实录。武宗微行出居庸关,上疏抗谏。世宗继位,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因“大礼议”受廷杖,谪戍终老于云南永昌卫。终明一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杨慎自幼聪颖,十一岁即能作诗。十二岁,写成《古战场文》,众人皆惊。进京后,写《黄叶诗》,为李东阳所赞赏,让他在自己门下学习。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中式辛未科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正德十二年(1517)八月,武宗微行出居庸关,杨慎上疏抗谏,被迫称病还乡。
此外,杨慎的父亲也是明朝的三朝老臣——内阁首辅杨廷和。
明世宗即位,被召至京师,任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爆发,杨慎与王元正等二百多人伏於左顺门,撼门大哭,自言“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世宗下令将众人下诏狱廷杖,当场杖死者十六人。十日后,杨慎及给事中刘济、安磐等七人又聚众当廷痛哭,再次遭到廷杖。杨慎、王元正、刘济都被谪戍。
杨慎动身前往戍地云南永昌卫。从前其父廷和当国之时,曾经裁撤锦衣卫冗员,有怀恨在心者趁机埋伏在途中,伺机加害杨慎。杨慎有所准备,处处小心。驰骋万里,到达云南之后,几乎一病不起。
两年后,杨廷和生病,杨慎得以短暂回家探视,其父病愈后又返回永昌。不久,率家奴协助平定寻甸安铨、武定凤朝文叛乱。嘉靖八年(1529),杨廷和病逝,杨慎获准归葬其父。此后,或暂回四川,或在云南省城,或停留于永昌,在各地均得到地方官员善待。
世宗因大礼议之故,对杨廷和、杨慎父子极其愤恨,常问及杨慎近况,大臣则回答杨慎“老病”,世宗才稍觉宽慰。杨慎听闻此事,更加放浪形骸。常纵酒自娱,游历名胜。《乐府纪闻》称他“暇时红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令诸妓扶觞游行,了不为愧。”终世宗一世,六次大赦,杨慎终不得还,按明律年满六十岁可以赎身返家,但无人敢受理。杨慎年近七旬时,曾返回泸州短住,不久又被巡抚派人押解回永昌。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卒於戍地。明穆宗隆庆初年,追赠光禄寺少卿,明熹宗天启时追谥文宪。《明史》有传。
喜藏书。早年,明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著述多至100余种,李调元刊《函海》时,曾作专辑收录所著之书。重要结集有《升庵集》散曲有《陶情乐府》。
文学
杨慎存诗约2300首,所写的内容极为广泛。因他居滇30余年,所以“思乡”、“怀归”之诗,所占比重很大。他在被谪滇时,妻子黄娥伴送到江陵话别,所作的《江陵别内》表现别情思绪,深挚凄婉。《宿金沙江》描写往返川滇途中的感慨:“岂意飘零瘴海头,嘉陵回首转悠悠,江声月色那堪说,肠断金沙万里楼。”以今昔行旅思情相对,衬出离愁的痛苦。
他临终前所作《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诗:“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叙述自己因病归蜀,途中却被追回的憾恨,深为感人。
他也有一些诗作表现了对人民疾苦的关怀。《海口行》及《后海口行》揭露豪绅地主勾结地方官吏,借疏海口占田肥私。他在诗中指出,“疏浚海口银十万,委官欢喜海夫怨”,并呼吁“安得仁人罢此宴,亿兆歌舞如更生”。他在《观刈稻纪谚》中托老农之语,说“乐土宁无咏,丰年亦有歌。惟愁军饷急,松茂正干戈”。表现了农民遇丰年,却因军饷赋敛沉重贫苦生活。其他如《宝井篇》《滇池涸》等,也是此类作品。
杨慎的写景诗也不少。他叙写云南风光,描绘祖国山河,颇有特色。《海风行》写了下关的风:“苍山峡束沧江口,天梁中断晴雷吼。中有不断之长风,冲破动林沙石走。咫尺颠崖迥不分,征马长嘶客低首。”气势雄伟,有雷霆万钧之力。而《龙关歌》:“双洱烟波似五津,渔灯点点水粼粼。月中对影遥传酒,树里闻歌不见人。”写洱海夜色,渔舟灯火,月映水波,细腻清新。当他来到有川南胜景之称的西昌泸山,看到这里的美景与火把节的盛况后,在此吟出了名句《夜宿泸山》:“老夫今夜宿泸山,惊破天门夜未关。谁把太空敲粉碎,满天星斗落人间”。此外,杨慎又有描述、歌颂历史英雄、忠臣义士以至耕夫樵叟的诗,其中也不乏佳作。
杨慎在前七子倡导“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复古风气较为流行的时候,能别张垒壁。他广泛吸收六朝、初唐诗歌的一些长处,形成他“浓丽婉至”的诗歌风格。如《滇海曲》12首、三峡《竹枝词》9首,描绘山川风情,颇得乐府遗韵。他的《垂柳篇》,深具初唐风范。《于役江乡归经板桥》:“千里长征不惮遥,解鞍明日问归桡,真如谢姚宣城路,南浦新林过板桥。”抒发行役倦苦的情怀,情致绵细,别出新境。杨慎又广为采揽“桑间濮上”的民歌的长处,以丰富自己诗作。如《送余学官归罗江》,全用绵州民歌,后缀四句送行语,构思新颖,别致清新。
杨慎对文、词、赋、散曲、杂剧、弹词,都有涉猎。他的词和散曲,写得清新绮丽。如(浪淘沙)“春梦似杨花”一首,描写细润,言辞华美流畅。散曲(驻马听)《和王舜卿舟行之咏》,写月下舟行幽景,江天一色,月光如水,并畅想驶入长空银河,意境优美,记叙细微。他的长篇弹唱叙史之作《二十一史弹词》,叙三代至元及明季历史,文笔畅达、语词流利,广为传诵。他的散文古朴高逸,笔力奔放。《汉杂事秘辛》事皆淫艳而言辞端雅,不见鄙秽。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规劝明武宗“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相谏诫,情挚意切,时婉时激。他的《新都县八阵图记》《碧峣精舍记》等也是记叙散文的佳品。另外他还著有《宴清都洞天玄记》《太和记》《割肉遗细君》等杂剧。
《谭苑醍醐》八卷亦皆考证之语,与《丹铅录》大致相出入,而亦颇有异同。引《水经注》载诸葛亮表云:“臣遣虎步监孟琰据武功水东,司马懿因渭水涨,攻琰营,臣作桥越水射之。桥成,遂驰去”。此事《三国志·诸葛亮传》不载,可补史阙。
杨慎在文学上既讲求文法,主张诗文用字要有来历,又反对极端的复古主义;反对诗史说;偏爱李白,亦好杜甫,对李白的身世进行了有价值的探讨。又辨李白为蜀之彰明人,历引其《上裴长史书》与《悲清秋赋》及诸诗句,以证《唐书》称白为陇西人及唐宗室之非,如此之类,考订辨论,亦多获新解。
儒学
- 揭示理学和心学都存在的弊端
杨慎说:骛于高远,则有躐等凭虚之忧;专于考索,则有遗本溺心之患。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问学”。故高远之弊,其究也,以六经为注脚,以空索为一贯,谓形器法度皆刍狗之余,视听言动非性命之理,所谓其高过于大,学而无实,世之禅学以之。考索之弊,其究也,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如华藻之绘明星,伎儿之舞呀鼓,所倡其功倍于(而效)小,学而无用,世以俗学以之。
“尊德性而道问学”,本为《中庸》所谓,但宋儒中,朱熹主张以究理问学为主,提倡研读经传,一依圣贤遗教去做,有偏重于“道问学”的倾向,陆九渊讥评其支离破碎;陆九渊主张学者从经典中解脱出来,求诸本心,认为“学苛知本,‘六经’皆我注脚”,有“尊德性”的倾向,朱熹斥责其尽废讲学。自南宋朱、陆相争以来,两家之学渐成水火之势,“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这对儒学发展影响甚大,诚如程敏政所说:“朱、陆之辨,学者持之至今。…其流至于尊德性、道问学为两途,或沦于空虚、或溺于训诂,卒无以得真是之归。此道所以不明不行。”
杨慎在这里则对朱、陆都进行了批评,指出陆学之弊在于“以空索为一贯”,趋简凭虚而入于禅,“学而无实”;朱学之弊在于“以杂博相高”,遗本溺心而流于俗,“学而无用”。在他看来,“经学之拘晦,实自朱始”,“新学(此指象山心学)削经铲史,驱儒归禅”,两者对学术风气和儒学的发展都产生了不良影响。这样,杨慎便全面否定了宋儒所倡通学。
对于当世流行的“道学”(即理学)和“心学”,杨慎亦持全面否定态度。他说:“道学、心学,理一名殊。明明白白,平平正正,中庸而已矣。更无高远亢(言)妙之说,至易而行难,内外一者也。被之所行,颠倒错乱,于人伦事理大戾。顾巾衣诡服,阔论高谈,饰虚文美观而曰:吾道民、吾心学,使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琢磨,以求所谓禅悟。此其贼道丧心已甚,乃欺人之行、乱民之俦,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何道学、心学之有?”他认为儒学本是“明明白白,平平正正”,“内外一者也”,但承袭宋儒之学风而流行于明世的所谓“道学”、“心学”,尽管名称不一,形式有异,而其实都是只知“阔论高谈”、“虚饰文词”,只说不行,“教人领会于渺茫恍惚之间而不可着摸”的空洞无用之物。其恶果,一是欺世,二是乱民,故皆为“圣王之所必诛而不以赦者也”。如此之“道学”、“心学”,根本背离了儒学的基本精神。
- 指出心学“削经铲史,逃儒归禅”,又点示理学同禅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其指出朱熹《中庸章句》所引程颐“活泼泼地”之类的话就是以佛家语录入章句,他说余尝评之曰:《说文》之解字,《尔雅》之训诂,上以解经、下以修辞,岂不正大简易。……至宋时,僧徒陋劣,乃作语录;儒者亦学僧家作语录……欲求易欲,反为难知;本欲明经,适以晦道矣!甚者因陋就简,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曰:我所述程朱之说,道理之谈,辞达意而已,不求工也。噫,左矣!这里所说的“以打乖筋斗入诗章,以闭眼合眉入文字”是陈献章(白沙心学)所为。可见,在杨慎看来,“学禅家”而导致儒学之“理”难知,圣道几晦,实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通病。
此外,杨慎认为,庄子所谓“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乃切要之言,丘长春所谓“世间之事尚不能究,况天下之事乎”乃正论。而邵雍、朱熹论天则是强不知为知,实为“妄说”。他说:“古论天文者,宣夜周髀浑天之书,甘石洛下闳之流,皆未尝言。非不言也,实所不知也。若邵子、朱子之言,人所不言,亦不必言也;人所不知,亦不必知也。……吾人固不出天地之外,何以知天之真面目欤?且圣贤之‘切问近思’,亦向必求知天下之事耶?”他还对宋儒鬼神之论予以批判,指出朱熹对《中庸》所谓“鬼神为德”之解有悖儒家作书之旨,曰:“宋儒解‘鬼神’二字,支离太甚,既以‘二气’言,又以‘造化’言;……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则有形有声,视之可见,听之可闻矣,岂不与《中庸》背驰矣?且《中庸》一书,本是平常之理,而引之高深虚地文字,又岂子思作书之旨乎?……故朱子引程、张‘二气’、‘良能’、‘造化之迹’诸说,移以解《易》之‘鬼神’则可,解《中庸》之‘鬼神’则不可。”所以,杨慎讥笑宋儒“杂博”、“支离”、“割裂”,如同“伎儿之舞迓鼓”,既“无古人之学,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学官衙鼓节也”。如此,不流入禅,借助于佛家之言以装饰门面,又怎么可能呢?
- 对阳明心学有所批判
杨慎借云南副使陈梦祥《六经》“一字一义皆圣贤实理之所寓,实心之所发”的话,职责陈献章“六经皆虚”论实“非圣人之蕴”,乃“佛者幻妄之意”。他说:“儒教实,以其实天下之虚;禅教虚,以其虚天下之实。陈白沙诗曰:‘六经缘在虚无里’,是欲率古今天下而入禅教也,岂儒家之学哉!”杨慎更怒斥王阳明为“霸儒”、“儒枭”,批评其以儒为表、以佛为里,证性见心、“驱儒归禅”,背叛了儒家的经义,说:“迩者霸儒创为新学,削经划史,驱儒归禅,缘其作俑,急于鸣俦, 俾其易人,而一时奔名走誉者,……靡然从之。”他又寓庄于谐地对人们何以会对阳明心学“靡然从之”作了分析,引其友之语道: 余友蒋兆晕芝善戏语而有妙理,尝论讲学之异曰:“宋儒‘格物致知’之说,久厌听闻,‘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一出,新人耳目。如时鱼鲜笋,肥美爽口,盘肴陈前,味如嚼冰,蚁而厌饫,依旧是鹅鸭菜疏上也。又如真旦看厌,却爱装旦;此北《西厢》听厌,乃唱南《西厢》。观听既久,依旧是真旦、北《西厢》出也。公多与辩,但徐徐俟之。”
- 对集理学之大成的朱熹批判最多、最烈
杨慎不仅从学术、思想的诸多方面批评朱熹,如在《陈同甫与朱子书》中讥朱熹自立门户,在《文公著书》中责朱熹“违公是远情”,在《俗儒泥世》里中斥朱熹“迂”,在《大招》《禹碑》《大颠书》中批评朱熹文学艺术上的失误,在《圣贤之君六七作》中指出朱熹史学上的纰漏。如何等等,难以详述,而且,他更一针见血地揭示道:朱熹之学“失之专”,“失之专者,一骋意(己)见,扫灭前贤”,用其自己的理学思想来诠释儒家经典,否定汉唐诸儒经说,以确立其自己的思想权威,而后儒不察,‘失之陋’,‘失之陋者,惟从宋人,不知有汉唐前说也’,只能仰朱熹之鼻息了:“高者谈性命,祖宋人语录;卑者习举业,抄宋人之策论”。这必然要导致“经学之拘晦”。
在《云南乡试录序》中更揭示阳明集心学之大成,鼓倡“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诸说造成了明代中后叶知识界的空疏浅陋,谓:“今士习何如哉!其高者凌虚厉空,师心去迹,厌观理之烦,贪居敬之约,渐近清谈,遂流禅学矣。卑焉者则掇拾丛残,诵贯酒魂,陈陈相因,辞不辨心,纷纷竞录,问则口,此何异叟诵诗、阍寺传令乎?究高者既如此,卑论者又如此,视汉唐诸儒且恧焉,况三代之英乎!”
经学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杨慎批评宋明理学是以其学术思想与方法为基础的,尤其是在经学研究中,杨慎非常重视从文献校勘、文字音义的训释与古代制度和思想的历史流变等多个角度考察儒家经典,以此为基础,杨慎对儒学有自己独立的见解。杨慎在《升庵经说》中每每以朱子的经注、经解作对比,发宋学之短而举汉学之长,于宋学不无补益,于后学不无启发。
杨慎突破明代学术界的“理学”与“心学”两家的理论禁锢,力图恢复汉学,建立一种新学风。杨慎提倡以怀疑的态度做学问,实开清代考据之先河。他指出治学的大方向:“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与此同时,杨慎还深刻批评了明代学者。杨慎敢于对经书权威性的解释大胆提出怀疑,并旁征博引、用多种证据以证成其说。他继承了前代鸿儒敢于怀疑的学术传统。杨慎痛感当时学界的死气沉沉、不思进取,提出:“古之学者成于善疑,今之学者囿于不疑。谈经者日吾知有朱而已,朱之类义可精义也。言诗者日吾知有杜而已,杜之窳句亦秀句也。宁可佞不肯为忠,宁可僻不肯为通。”杨慎为学,反对明代空疏学风,痛斥明代学者泥于成说,如有訾议者,“辄欲苦之,甚则鄙之如异域,而仇之如不同戴天一的“竺癃沈痼”,主张博通约取,笃于实际,对后世学者影响深远。
杨慎是较早进行专门音韵研究的学者,单行著作有《古音余》、《转注古音略》等十余种。他认为:“音韵之原,起于唐虞之世。《舜典》日声依永,律和声是也。吴才老、沈约都祖法于此。”(《丹铅总录·卷十九》)他善于从文字的音义上考虑,通过古音通假,阐明诗义。杨慎认为古韵语中不押韵之处,并非本就如此,而是古今音变化造成的。在《升庵经说》中,他关于《诗经》古音的研究有数十条之多。如《瓠叶》“有兔斯首”,斯、鲜音相近,训白。“《左传》‘于思于思’,服虔注:思,头白貌。思、斯字异而音同。”这些观点虽有的为前人遗说,但从古音通假的角度加以阐释,意思更加明白。
杨慎重视训诂注经。他批驳“昔人乃注《本草》误杀人而注《易》误无害”(《丹铅续录,卷一》),努力探讨古人训诂,以为“古人训诂缓而简”。但他又主张”不可溺训诂”(《丹铅总录·卷十三》),反对“章句之病,党枯护朽,守缺保残”(《丹铅总录·卷二十二》)。如《关睢》“窃窕”古有幽闲、深宫、美心为窃,美容为窕等说,杨慎《升庵经说》为证实郑玄、孔颖达的“窃窕深宫”说,一口气举了十二条证据,以证明“窃窕”有深的意思,并非言德。
著述
杨慎一生刻苦学习,勤于著述,是有明一代著名的博学家。他不仅对经、史、诗、文、词曲、音韵、金石、书画无所不通,而且对天文、地理、生物、医学等也有很深的造诣。如他任翰林时,明武宗问钦天监及众翰林:“星有注张,又作汪张,是何星也?”众张口结舌,无以对答,独杨慎从容对曰:“柳星也”,并历举《周礼》《史记》《汉书》等文献资料加以说明。他预修《武宗实录》,事必直书,不为尊者讳。他在长期流放中,仍然“好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杨慎传》)。在云南永昌边塞荒凉地区,尽管图书资料奇缺,升庵仍嗜书成癖,“书无所不览”,经常对人说:“资性不足恃,日新德业,当自学问中来。”(《明史·何孟春传》)他认为要“知天下”,一是依靠“躬阅”,从亲身经历中获得知识;二是依靠“载籍”,从别的记载和书籍中取得。因此,他不仅刻苦读书,手不释卷;而且每到一处,就对当地风俗民情进行调查了解,努力学习当地民族语言,从亲身经历与实践中丰富自己的知识。他以被逐罪臣的身份,仅凭自己苦学、实践、记忆,在滇南时就写出了不少笔记、选本以及许多注释性书籍。如《南诏野史》《云南通志》《云南山川志》《慎候记》、《南中志》《滇载记》《记古滇说》等书。
据《升庵杨慎年谱》的记载,杨慎平生著作有四百余种。所以,《升庵外集》序称:“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明史》本传称:“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
藏书
杨慎喜藏书,当时司礼监大藏经厂,贮列朝书籍甚富,他多次至阁中翻览书籍。据传曾攫取数册《永乐大典》据为己有。其后主事李继先奏命查对时,戏以窃书之名。
家有“双桂堂”,为读书、贮书之所。曾编撰有《杨氏书目》,明末藏书家王道明在其《笠泽堂书目》中有记载。清初姜绍书记明一代藏书家,将他与杨士奇、吴宽、茅坤、宋濂等并列。
书法
杨慎工于书法,王世贞《国朝名臣遗墨跋》称杨慎“以博学名世,书亦自负吴兴(赵孟頫)堂庑”。朱昌颐《跋杨升庵诗扇》也说:“书法尤超迈绝伦,至今滇南尚多留刻”。其书论主要见于《墨池琐录》、《升庵书品》、《法帖神品目》等。
绘画
杨慎亦善写兰。王文治《杨升庵画兰长卷跋》称:“杨升庵画兰卷子(长至四丈),疏密反侧,朝烟晚露,皆能毕肖其形。”其画论有《升庵画品》《名画神品目》等。
文献学
杨慎的文献学思想不仅自成体系,而且充满着辩证法的思维;他重视训诂考据和博学,同时又强调实践经验,重视正史书籍和名家注疏但不一味盲从。正史书籍由于其“不寓褒贬”“直书其事”的特点和它自身带有的权威性,因此类史籍都可以作为研究文献、考据文献的重要证据。杨慎对正史书籍便颇为重视。无论是天文地理、鸟兽花木,还是宫室物用、人品订讹,《丹铅总录》都充分依托史籍。
从《史记》《汉书》《三国志》到《新唐书》《旧唐书》和《宋史》,引用范围极其广泛。尽管如此,杨慎依然抱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史籍,并不迷信权威,先后论证过《史记》《后汉书》等书中的问题。如在“司马迁设史”一条中提到,《左传》有云:“齐侯朝于晋,将授玉。”而司马迁误读玉为王,所以在《史记·齐世家》中误以为齐国欲尊晋景公为王。执玉即为执圭,古代凡诸侯相朝,必定互相授受以玉为礼,这是当时的一种规制。还有在“玄鸟衔卵”一篇中说,《诗经》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司马迁对这种现象的描述是“玄鸟翔水遗卵,简狄取而吞之”。杨慎对太史公的这个解释并不认同,杨慎驳道:此处并非实指,非指玄鸟把卵排出,被简狄吃掉而怀孕,而是《诗经》在此处用了一种兴深意远的方式,来说明商这个尊贵的孩子是上天的指派。玄鸟是请子的候鸟,即春燕,此处“若曰仲春之月祷而生商,斯为言之不文矣”。且在《诗经》中有找到多处例证,《诗经》有“维岳降神,生甫及申”,也是为了说明孩子出身的高贵,而不是说甫、申为岳神所生。另外,杨慎对名家的注疏也很重视,无论是郑玄、李善的注,还是颜师古、朱熹的注,杨慎都很看重,并且在考据字书音韵的时候经常引据。但是杨慎并不因为他们是大家权威就一味盲从。比如在“郑玄解经有不通处”中,郑玄认为“宗祀文王”是以文王为宗,而杨慎认为此处“宗”并非是以文王为宗,而是“宗”在此处通“尊”,并且举出《祭法》中“祖文王而宗武王”和《左传》中“宗”通“尊”的例子来证明,如“召伯宗”通“召伯尊”,“尊卢氏”为“宗卢氏”。在“朐忍辨”一条中,对颜师古因为“朐忍县”的“朐”和“劬”形似而注音错误的问题也进行了纠正。 [95]
杨慎在运用文献考证研究的方法上,不仅能吸取前人之长,而且在重视子部、俗文学与金石方志等资料方面独有建树。在《丹铅总录》中,处处可以看到杨慎对子部的引据。不论是在考证官爵礼乐、字学订讹,还是史籍博物等等,都十分重视子部的作用,从先秦诸子的著作,到《淮南子》《水经注》乃至佛经,只要可以作为考据的论证,杨慎都加以引证。比如在“石墨”中对石墨一词的考据中,就先后用到了《水经注》和《本草纲目》。“湛涔同字”一条中就多次引用《淮南子》。而在“八功德水”中就用到了佛经中的内容。杨慎不仅考证多用子部,而且对子部也多有考证。比如在“老子述而不作”中对《老子》内容的考据,在“管子注”中对《管子》近世翻刻中注解出现的问题的订正,在“鬻子”一条中,通过搜集他书引用已散佚《鬻子》书中的内容,来对《鬻子》进行辑佚。这些都充分说明了杨慎对子部的重视。
金石文献是研究古代文献的重要资料,因而杨慎在《丹铅总录》中也很注意运用金石文献。如在《琐言》部分中,谈到省字时说到一种语法现象:凤凰同书,省下作皇,鹦鹉聊文,省下作武。并且举出《石鼓文》中“旭日杲杲”同样是因为省字,而书作“旭日杲=”。还有在“黔首”一条中,在考证黔首之意时,就用到了李斯《峄山刻石》中的“黔首康定”,并说太史公便是因为这句判定“秦名民曰黔首”。
文化事业
在明代,云南被说成是“蛮荒瘴疠之乡”或“不毛之地”,所以朝廷才会把罪犯发配到那里去服刑。杨慎来到云南后,经过生活实践,发现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大汉族主义的思想偏见。他认为,云南和内地的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联系,中原汉族和云南的多民族人民都是炎黄子孙,中国是统一的国家,对待各民族的群众应该一视同仁。因此杨慎始终不忘国事,致力于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增强云南地区的国家认同感。
他曾身穿戎装,召集童仆、学生、邻里一道保家卫国,为平息大规模的“安凤之乱”立下大功。当他发现昆明豪绅以修治海口为名,勾结地方官吏强占民田坑害百姓时,正义凛然地写下《海口行》等诗痛加抨击,并写信给云南巡抚,要求制止劳民伤财的所谓水利工程。他与丽江土司木氏交情深厚,指导木氏诗文创作,整理少数民族典籍,为传播民族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
杨慎在云南开展讲学活动,传播中原文化,培养云南本地的文人学者。杨慎在云南三十多年,经常到各地讲学授徒,为当地造就了大批学有成就的人才。据《滇南闻见录》记载,他“尝于临安教授生徒,多所造就”。《安宁州志》说他:“居城东遥岭楼,尝讲学于上。”《大理府志》描写,自杨慎来后,“郡人士威师之”。
杨慎在云南的学术同好和门人数以百计,其中,大理人李元阳是和他关系比较密切的一位,两人曾共同参加撰写《云南通志》。李元阳在《送升庵先生还螳川客寓诗序》中,详细地叙述了杨慎在大理点苍山感通寺讲学的盛况:“各族士子皆从游问学。”在杨慎的学友和门生中,以张含、王廷表、李元阳、唐绮、杨士云、吴懋和胡廷禄七人最为有名,人称“杨门七子”,意思是把他们比作宋代苏轼门下的“苏门六君子”。他们都有较高的文学成就,两人是举人,五人是进士。特别是在诗歌创作方面,他们都取得了很深的造诣,这是和杨慎的奖掖扶植分不开的。杨慎本人也曾自豪地称赞说:“七子文藻,皆在滇云,一时盛事。”
据统计,云南到元代为止,可考的著作只有八种。到明代正德年间,著作达四十余种,著书者二十余人。但到了明嘉靖以后,情况就大大不同了。嘉靖至明末,云南的著述增至二百六十余种,著书者也多达一百五十余人,而嘉靖及稍后一些时候的著作,就达到了一百余种,它们的撰写,都直接或间接地与杨慎有关。这说明在杨慎的影响下,当地出现了一支人才队伍,云南的地方文化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杨慎终身流放滇南,但他情系故里,多次回到家乡四川,为家乡文化事业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编写了《全蜀艺文志》,这是一部四川地方历代诗文总集,全书64卷,收录诗文1800多篇,共计140多万字,广收博采汉魏至明有关四川诗文。 《全蜀艺文志》对巴蜀文化的传承有重要意义,又因杨慎的名气,其成书后被多次刊刻、抄录,流传颇广。
褒
李贽在《续焚书》中说: “升庵先生固是才学卓越,人品俊伟,然得弟读之,益光彩焕发,流光百世也。岷江不出人则已,一出人则为李谪仙、苏坡仙、杨戍仙,为唐代、宋代并我朝特出,可怪也哉!” 李贽恨不得“余是以窃附景仰之私……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读《升庵集》》
袁宏道:“人有言曰:‘胸中无万卷书,不得雌黄人物。’然书至万卷,不几三十乘乎?除张司空外,更几人哉。吾于汉刘向、唐王仆射、宋苏子瞻见之,然自子瞻迄今又三百余年矣,吾于杨升庵、李卓吾见之。”(《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
王夫之称杨慎诗“三百年来最上乘”。(王夫之《明诗评选》卷五)
周逊《刻词品序》中称他为“当代词宗”。
王世贞:“明兴,称博学、饶著述者,盖无如杨用修。”
焦竑十分推崇杨慎,曾花很长时间专心搜集杨氏著作,经过校对订正,编辑成《升庵外集》一百卷,刻板传世,并在《升庵外集题识》中盛赞道:“明兴,博雅饶著达者无如杨升庵先生。”
顾起元在《升庵外集序》中说:“国初迄于嘉隆,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毋逾升庵先生者。”李慈铭:“有明博雅之士,首推升庵;所著《丹铅录》、《谭苑醒酬》诸书征引该博,洵近世所罕有。”
胡薇元《岁寒居词话》说:“明人词,以杨用修升庵为第一。”
钱允治《类编笺释国朝诗余》选杨慎词达118首,占了整部词选的四分之一。
《明史·杨慎传》:“杨慎博物洽闻,于文学为优。”
《四库全书总目》:“慎以博洽冠一时,其诗含吐六朝,于明代独立门户。”
明末朱之瑜晚年讲学日本,教育日本学生安东守约说:“明朝文集极多,好者亦寥寥……如杨升庵、李空同集,极佳。”(《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三》) 小宅生顺问:“扬雄、司马氏鸣汉家,眉山三苏及陆游等鸣宋家,不知今亦有如此人哉?”朱之瑜回答说:“国朝有宰相之子杨升庵讳慎者……”(《朱舜水集》卷十一〈问答四〉)
简绍芳〈升庵先生年谱〉说:“公颖敏过人,家学相承,益以该博。凡宇宙名物之广,经史百家之奥,下至稗官小说之微,医卜技能、草木虫鱼之细,靡不究心多识。……平生著述,四百多种…学者恨未睹其全也。”顾起元《升庵外集序》说:“文人学士著述之富,无逾升庵先生者。至其奇丽奥雅,渔弋四部七略之间,……唐宋以来,吾见罕矣。”
纪昀更赞曰:杨慎“可以位置郑樵、罗泌之间,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矣。”
近现代的陈寅恪说:“杨用修为人,才高学博,有明一代,罕有其匹。”
贬
陈耀文,对杨慎的博学颇感不服,特作《正杨》一书,指出《丹铝》诸录中的150条错误。万历年间,胡应麟仿杨慎《丹铅录》而作《丹铅新录》、仿杨慎《艺林伐山》而作《艺林学山》,一面订正杨氏笔误,指出:“千虑而得间有异同,即就正大方”;一面不满于陈耀文“哓哓焉数以辨其后”,自以为“求忠臣于杨氏之门,或为余屈其一指也天”。
胡氏此举,被“时人颜曰《正正杨》”,朱国桢对之评曰:“(自)有《丹铅录》诸书,便有《正杨》、《正正杨》,辨则辨矣,然古人古事古字、彼书如彼、彼书如此,原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未见其二,哄然相驳,不免为前人暗笑。”迨于清世,四库馆臣既说:“慎于正德、嘉靖之间,以博学称,而所作《丹铅录》诸书,不免瑕瑜互见,真伪互陈”,又说:“耀文考证其非,不使转滋疑误,于学者不为无功。然衅起争名,语多攻讦,丑词恶谑,无所不加,虽古人挟怨构争如吴缜之解《新唐书》者,亦不至是,殊乖著作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了杨慎29种著述,一一加以考评,虽承认杨慎“博洽冠一时”,《丹铅》诸作“疏殊虽多,而精华亦复不少”,但就总体言之,还是站在正统立场,对杨慎其人其学每多贬抑,如说他“好伪撰古书,以证成己说”,责他“取名太急,稍成卷帙,即付枣梨, 为编,只成杂学”等等。由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官修之书,故自面世流传后,杨慎即长期被冷落,一直不被重视。流风余波所及,以至近百余年来的中国儒学世、中国思想史著作中,多无杨慎的一席之地。